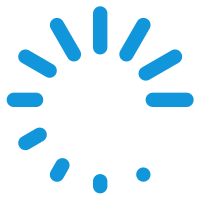“对撞机对撞成功后,我们在黑大理石碑上用金字刻下了所有‘参战’单位的名字。”讲起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,已近八旬的柳怀祖仿佛回到了改革开放初期那个争分夺秒的年代。身为对撞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,他曾体会到的,是战士“豁命去战斗的精神状态”。
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,1984年动工,1988年首次对撞成功。速度之快,让国际物理学界都为之震动。
30年后回看,这个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我国高能物理国际地位的大科学装置,身上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。
从“七上七下”到“不再犹豫”
要探索物质的微观结构,就得把它打碎。打碎物质的“炮弹”是高速粒子束流,而加速器就是发射这种炮弹的武器。
对撞机是加速器的一种,它让两束高速粒子束流相撞,产生更大的能量,不过,让两束比头发丝还细的、接近光速的粒子流相撞,是个极复杂工程。
早在1956年,我国就提出过建造高能加速器的计划,但都“只打雷,不下雨”。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正式动工之前,高能加速器更是历经了“七上七下”:之前六次,刚计划就偃旗息鼓;第七次的“八七工程”,预研工作已开始,地址也已选定,但1980年随着国民经济调整,基础建设紧缩,它又被终止。
“那时大家都很茫然,七嘴八舌,什么声音都有。”连物理学家杨振宁也不赞同高能加速器方案,还曾对柳怀祖说,有这些钱,为什么不去造铁甲车(坦克)。
“有波折并不奇怪。”柳怀祖分析,“基础科学有什么用?在国家财力比较困难的时候,科研经费的天平应该往哪边倾斜?这是世界各国都会遇到的问题,直到今天,它也仍然是个问题。”
而且,在那个年代,我国懂加速器建设的人并不多。到底要建怎样的加速器,建成之后要用来做什么,认识并不清晰。
上世纪80年代初,邓小平指示方毅副总理就建造高能加速器问题,广泛征求国内外科学家的意见,充分论证,提出方案。方毅组织了全国十几个研究和工业部门的60多位专家进行反复论证。
综合各方面意见,大家大体都赞成李政道、吴健雄、袁家骝及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主任潘渃夫斯基等人的建议——先建造一台2×2.2GeV的正负电子对撞机。方案提出后,邓小平拍板,亲自批示:“我赞成加以批准,不再犹豫。”
“方毅副总理组织的讨论很关键,讨论透了,有了清晰的物理学目标。”柳怀祖说。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覆盖的能量区间内,有大量粲物理前沿研究工作可做,科研人员才得以在后来的日子里,窥见物理学的奇特风景。
1984年10月,邓小平出席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开工典礼,为奠基石培上第一锹土。他对周围人说:“我相信这件事不会错”。
改革开放下的自力更生
聂荣臻曾这样评价——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我国科学家继原子弹、氢弹、人造卫星、核潜艇之后取得的又一伟大成就。
和原子弹、氢弹不同的是,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国际合作的产物。它是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打开国门对外交流后,在中美两国政府间签署的“中美科技合作协议”正式合作框架下开展的第一个研究合作的实体项目。“它是我国科技领域开始国际合作的里程碑。”柳怀祖说。
那段时间,在科技合作上,美方给予了中国大量支持与帮助。
一个标志性的例子是计算机。正负电子对撞时产生的各类粒子状态的几万路电信号,都要由电子计算机进行分析处理。为了帮助中方从美国进口当时尚禁止出口的、世界上最为先进的VAX8550大型计算机,潘诺夫斯基到美国国会作证。他说:“你可以问全世界所有的高能物理学家,哪一个会告诉你们说高能物理研究不需要大型计算机。”最终,美国国会同意出口此计算机给对撞机项目使用。
尽管如此,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原则也很明确:在充分学习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,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计划和建造,也就是“能自己干的就自己干”。
在柳怀祖看来,这是全国几百个工厂、研究所、高等院校的上万科研人员、工人、干部和解放军战士参与的一场“高科技战役”。
他举了个例子。当时,谱仪的端盖簇射计数器由上海5703厂组装。组装好后,运来北京,由于运输震动,产品扭曲变形。为了避免再出问题,上海5703厂干脆将整个安装班子全部拉到北京,现场组装。一些年轻女工把出生不久的孩子放下,在北京一呆就是一二十天。
参与项目的上万人,没有假期、经常加班,连轴转也是常事……没人计较得失、报酬。柳怀祖记得清楚,当时的加班夜餐补助不到一块钱,一包方便面就要8毛钱。“泡碗面再加个蛋,还得倒贴钱。”
1988年10月,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如期实现正负电子束的对撞。当年10月24日,邓小平到了四年前他亲自奠基的地方,即席发表讲话——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。
如今,运行30年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已进行了升级改造,在世界同类型装置中继续保持领先。近日,我国科学家提出的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也发布了《概念设计报告》,若该方案顺利实现,我国或可一跃成为世界重要前沿基础科学的领头羊。